

《女人韵事》。 制图:李洁
在预料中的,《阮玲玉》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出票最抢手的影片之一。好的表演,是电影不败岁月的硬通货,甚至可以说,电影视听的技法和修辞往往带着清晰的时代印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表达,但表演不是,带来强烈戏剧震撼和感染力的表演,如超然于时间之外的法术。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桃花泣血记》《孤苦盲女阿玲》《女人韵事》等影片,不同年代的女演员在风格迥异的作品里付出了各自充满生命能量的演出,再现于大银幕上的她们,为表演这个工种确立了不可轻易跨过的专业门槛——顶流的表演,综艺节目是无力复制出分毫的,它更不是能在茶余饭后、社交媒体上任人非议的话题。
对现实的准确素描所呈现的画面,是对现实的陌生化
在充斥着演员们煽情小作文和对“炸裂式表演”炸裂式吹捧的浮夸语境里,于佩尔主演的《女人韵事》可以看作永恒的清流。于佩尔是非常罕见的那类,能持续地给同行和这个行业带来启发的演员,譬如在《女人韵事》里,她创造了一种既简洁清晰又富于变化的表演,有强悍自我意识的假面,覆盖着混沌迷失的意识世界,有对日常极度准确的刻画,又和现实保持微妙的距离,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制造了无与伦比的戏剧震撼力。
夏布罗尔导演的这部电影,《女人韵事》是个很容易引发歧义的译名,直译“女人的故事”更妥当些,它确实是字面意义的非常时期下的一个女人和她身边一群女人们遭遇的冷酷事件,并无罗曼蒂克的“情韵”。影片背景是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诺曼底地区,承受生育、饥饿、劳累重重苦役的女人们为了活得好一点无所不用其极。片中桩桩件件都不是正常情境中的正常事件,稍有不慎,就是呼天抢地的狗血情节剧。但于佩尔给出了克制冷静的表演,严格控制自己表情和身体细节,她在烧水、打扫房间、照顾孩子吃喝这些微小的、反戏剧化的行为中,撕开了一个道德模糊的反常世界。当她行迹败露而下狱,在囚禁中得知自己将被当作“败德典型”处死时,于佩尔仍没有允许自己进入撕心裂肺的失控状态,这个角色情感最浓烈的时刻,也只是像大理石雕像裂了一道缝,但仅靠着这道裂缝,也足够暴露黑暗世界的伦理风暴。在夏布罗尔的镜头下,在于佩尔的身上,谨小慎微的日常和惊世骇俗的背德是一体的,对现实的准确素描所呈现的画面是对现实的陌生化,从中升华了戏剧的震撼,以及戏剧对现实的反思。
表演的尽头是摆脱表演的控制,而非“成为角色”
于佩尔的表演提供了一种生动的演示,即绝好的表演总是准确的控制和开放的意义同在。而在《孤苦盲女阿玲》里,岩下志麻演示了极致开放性的表演可以抵达的境界。
岩下志麻最广为人知的银幕形象,也许是《秋刀鱼的味道》里待字闺中的小女儿,那年她21岁,在影片的结尾一袭盛装和父亲道别,笑容一尘不染,那个回眸的画面是青春定格的偶像之美,是一个召唤逝去时光的华美符号,承载着小津安二郎导演的无限伤怀。
而后在和筱田正浩导演的频繁合作中,岩下志麻仿佛打开了一个女演员的多重平行空间。比如同样参与今年电影节展映的《心中天网岛》中,她一人分饰婉转多情的风尘女子小春和忍辱负重的家庭妇女阿御。这是部实验感很强的影片,“一个男人因出轨而同时愧对两个深爱他的女子,三人因为情感的死结而最终结束各自的生命”。这原本是一部经典的“净琉璃”作品,即演员控制人偶的舞台剧,筱田正浩大胆地探索影像和舞台的边界,让真人演员扮演“净琉璃”,在近景和特写镜头下,这看起来是个寻常的婚外恋情节剧或江户时代风俗剧,而拉远至中远景,导演一再强调舞台的存在感和扮演的穿帮感。岩下志麻分饰两个差异很大的女性角色,与其说她展示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可塑性,不如说,她演出了“表演这回事”。
表演的尽头,是摆脱表演的控制,而非低层次的“成为角色”。在《孤苦盲女阿玲》里,筱田正浩开篇用几个空镜就明确了影片追求的情韵:雪落大地,草木荣枯,在茫茫世间,个体的命运和自然的流转一样,循着个体意志所无法控制的无情的节律。在水上勉的小说里,阿玲孤苦的一生承受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但她人生厄运的开端,是她不愿意“灭人欲”,是她出于好奇想要让生命展开如其所是的模样。筱田正浩抓住了极有象征感的一幕,用凄艳的影像再现了:少女阿玲在雪中行走时来了初潮,血落在雪地上,是一朵一朵鲜红的花。在这部电影里,岩下志麻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不在于她赋予了“阿玲”特征,正相反,她的一举一动是去人性化、去特征化的,她成为了氛围感的存在,融入了她行走的天地之间。就像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下的:“像最低级的植物,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这是原始性的顽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记者 柳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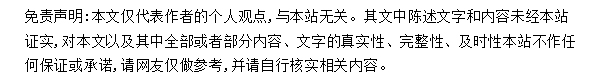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